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大家知道有哪些吗?彭桓武做出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精选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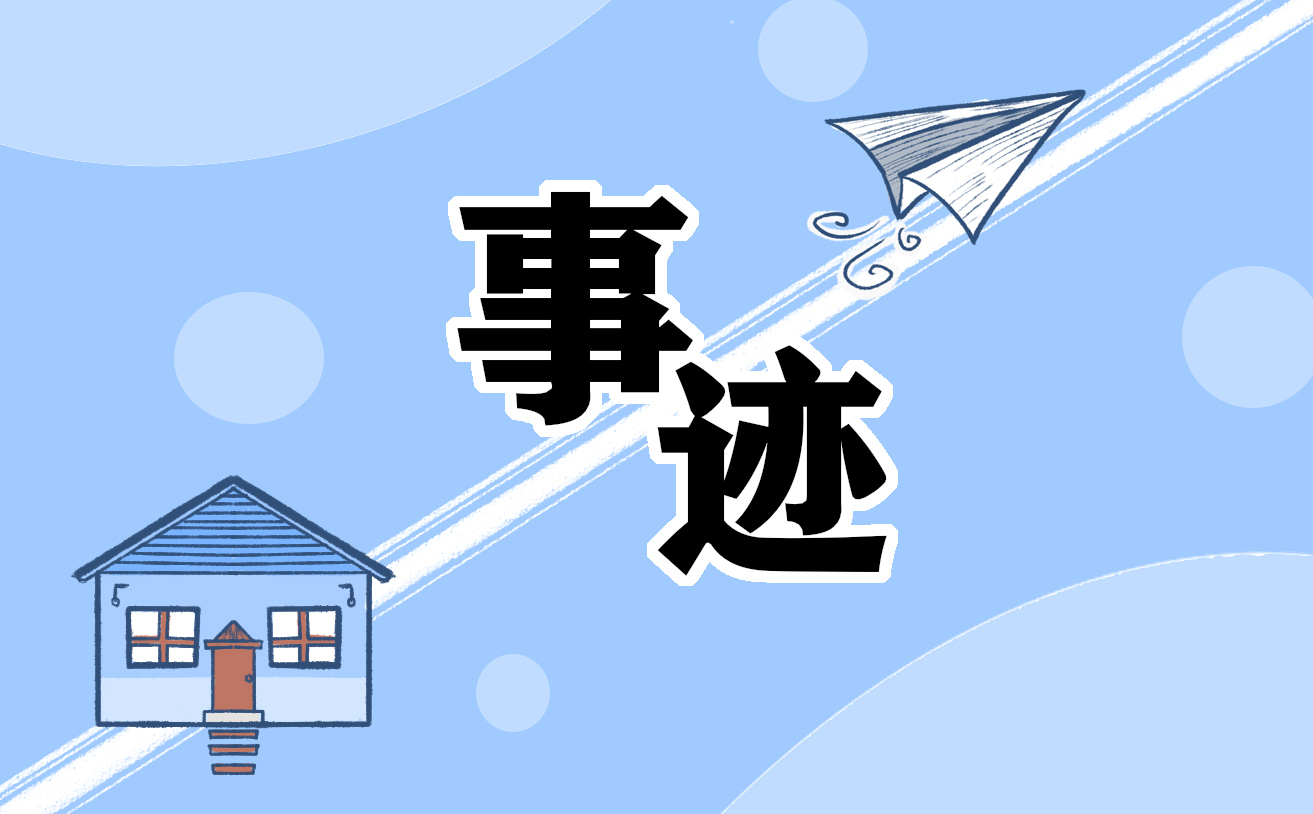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篇1】
他出生于20世纪初,就在他出生的翌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幼时的他体弱多病,两岁多还不会说话,但却已经会计算简单的算术题了。
他小学时基本病休在家,但期末考试还是按时参加,且每次考试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
15岁时,他就开始通过英文教材自学物理学和微积分。
16岁时,他从敬重的两位历史名将的字号中各取一字为自己重新取名,激励自己树立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20岁时,从清华物理系毕业。进入中国理论物理开山祖师周培源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研究广义相对论。
由于周培源先生一直在国外,加上战乱,论文完不成,只好肄业。跑到云南大学教书,月工资100中央票,比当时的省长还高。
1938年,他获得了留学英伦的机会,为了追随心中的物理大师马克斯·玻恩,他放弃了去剑桥大学,而选择了爱丁堡大学。
玻恩,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曾是该校物理系主任。
作为波函数统计阐释的提出者,玻恩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有德国的海森堡,奥地利的泡利,匈牙利的魏格纳,意大利的费米和美国的奥本海默等众多20世纪物理学天才在其门下受教。
由于受到纳粹迫害,这位科学大师来到了不列颠的这所古老的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依然保持了一个特别的癖好——喜欢招收外国人和女生做研究生。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篇2】
彭桓武还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深知,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接力。他在科研工作中,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他的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为我国的科技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这些人才在东风41等项目的研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传承了彭桓武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彭桓武的一生,是为科学事业奉献的一生。他淡泊名利,一心专注于科研工作。他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地位,只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他的精神如同东风41导弹发射时的烈焰,照亮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道路。
在今天,当我们为东风41的强大威力而自豪时,不应忘记彭桓武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辛勤付出。他们是我国科技事业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永远铭记彭桓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篇3】
彭桓武到玻恩处的时候,已有一位师兄在那里,他在用量子力学做凝聚态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玻恩和他商量给我出个题目,就是计算金属原子热振动的频率,而且建议我用弗勒利赫(Froehlich)边界条件和微扰法做。我一看就发现一级微扰好做,既简单又漂亮。由于简谐运动是位移的二次函数,位移就是微扰变量,因而计算频率一定要做二级微扰,但二级微扰就相当困难。我采用另外的方法,即作一变换。在变换空间里恢复了晶格的周期性。当然动能、位能和算符都变了,但由于恢复了周期性的边界条件,因而采用正规的微扰理论做到二阶并不困难。不过由于当时的哈特里—福克(Hartree-Fock)近似不能得出关联能,因而振动频率做不准,只求得了弹性模量。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可算只做了一半。但我以后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前些时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计算关联能的框架。从1940年交博士论文直到现在90 年代,这个问题在头脑里呆了半个多世纪。可见有的研究课题够你想一辈子的。关于周期性边界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拉曼(Raman)和玻恩就此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当时似乎是坚持这一边界条件的玻恩占了上风,因为理论的结果很好。拉曼从分子的观点出发认为任何实际的晶体都不存在周期性边界条件。我觉得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不应厚此薄彼,就像搞金属,量子力学可以采用布洛赫(Bloch)函数也可以采用旺尼尔(Wannier)函数一样。
后来我到爱尔兰的都柏林听海特勒(Heitler)讲量子化学课。我对量子化学一直有兴趣,因为我也学过不少化学。但我对量子化学也是一直不满意。因为量子化学是物理学家做的,而物理学家并不知道化学的真正要求所在。就拿化学反应中键能的变化来说,量子化学不管分子的大小,一概当成一个物理问题来计算电子的能量,直到原子内部K 壳层的能量都一视同仁。于是一个电子的能量就高达上百电子伏,可化学键能不过在电子伏的数量级,在化学反应中键能变换的差别就更小了,还不到1电子伏,结果是每个电子能量都算出来相加,再总能量相减,变成大数相减,其误差便可想而知。再有,基函数选得如何连自已也不知道精确度怎样估计,又引进了误差因素。因此这样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实际上这方面只要计算键能部分,计算差别,而内层电子的能量并不重要。因此我曾建议用键函数,而不用每个电子的波函数。当时想做的是CH4,化学家称之为标准状态。只要算出 C-H与C-CI两个键即可算出五个分子,即 CHnCl4-n(n=0, 1, 2, 3, 4),还可以自治核对,自然误差就小。求得键波函数,键—键相互作用还可扩展开去深入研究。这是我转到搞原子能之前最后一位研究生的工作,可惜并没有完成。前几年听说有人搞量子化学要采用双电子波函数,其实键函数就已是双电子波函数。
量子化学的缺点说明不能用单纯的物理观点搞化学问题,不同的问题应当有不同的观点。目前的量子化学其实只是物理。我认为应当将量子力学同物理化学结合起来,建立量子物理化学。例如电负性的问题,定义有好几个,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是量子物理化学。
我自己搞得比较深入的是场,电磁场、介子场。场是无穷个粒子的量子力学,有无穷个自由度。给定场,作傅里叶变换,系数即座标。无穷个粒子就有无穷个座标,因而引起发散的困难,我也为之花过很多精力。游特勒提出不必理会发散问题,保留项即为阻尼效应。我曾试用阻尼理论解决介子场的发散困难,不过没解决电磁场的发散困难,因为收敛不了,还是欠了帐。我现在想用做关联能的方法再做一下。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如狄拉克,大都不满意重整化理论,因为数学不干净,不严格。我也不满意。我现在想追求的是数学严格的方法。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篇4】
彭桓武本人在这一生的学习中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是主动请教。记得上初三的时候,物理老师讲了个透镜公式 1/f=(n-1)(1/R1-1/R2)。当时我以为所知道的物理公式都是由实验得出的,看到竟然有这么复杂的公式,甚觉莫名其妙,我便去问老师。我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北大毕业的好老师。他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借给我一本北大用的英文版大学物理教科书,指着上面的一幅图对我说,解释就在这里。我一看就清楚了,原来这个公式也有实验基础,就是折射定律,其余都是数学推演,主要是用几何学,而且我自己也做出来了。这件事我一直铭记在心,因为我从中得到很深的教益。一是看到了理论的作用,实际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物理理论。理论和实验一结合,即使是很复杂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二是我的英文就此在初三时期就过关了。再有,我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启发式教育的积极效果。
后来我到英国留学,师从著名学者玻恩(Max Born)。在阅读一本专著时碰到一个散射公式,是用波动力学求解的。波函数写成入射波与散射波的和,而散射的强度需用波函数的二次式计算,但其中交叉项则被略去,然而这些被略去的项在数量级上同保留下来的项不相上下,似乎照理是不该略去的。我便带着这个疑惑去请教玻恩,他给了我一个很精彩的回答。测量散射波是不能在入射波经过的路途中进行的。入射波虽然通常用平面波描写,但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宽度的,就同光束的宽度受光阑限制一样。在散射方向的测量处,已在入射波的宽度之外,其入射波的幅度应为零,自然也就不出现交叉项了。换句话说略去交叉项恰恰是反映了物理的实在。他的回答告诉我做理论研究一定要使理论能正确地描写实际情形,就是说要妥善处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这是做学问的一大关键所在。
以上两个例子都给了我很大的收获。但我想如果我不主动发问,即使有再好的老师,即使大师级的人物在身旁也是得不到那么大的收获的。因此我深刻体会到,主动请教是做学问的另一大关键。
其次是要处理好学习的深度与广度、简单和繁杂、近期安排与远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以便彼此间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实行的是选课制。我在进清华之前已读过汤姆逊(Thomson)的《科学大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对于科学的体系已有了大概的了解,并且也能确定哪些课程简单一些,哪些课程复杂一点。于是我入学的时候就将四年的选课表统统拿来,根据繁简、深度和近期远期之间的关系统一选择安排四年所应修读的课程,制定出整整四年所应达到的目标。自然科学课程中我只选物理和化学深入学习,数学只是去旁听并不选课。另外选了一门比较轻松的课程社会学,本来还想选解剖课,因为我想对生物学来说解剖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后来没有做成。我觉得只要你深入地学好一门课,那末推而广之,再学相近的科目就也能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深与广是学习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物理学比化学简单,化学又比生物简单,根据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我是先学物理再学化学。最有趣的是学心理学。我找了个高年资的同学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一边谈心理学。他告诉我心理学有所谓三大学派,我便去借了三本书,一派一本,书看完了,心理学也就算学了。
彭桓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事迹【篇5】
从他16岁踏进清华园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中间隔了不止30年;从他的故乡长春,到北京,到昆明,到英国,到爱尔兰,再到青海,这期间跋涉了不止8000里。
1978年,彭桓武在完成国防科研任务,调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之后,应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于同年10月至1979年6月开设理论物理课程。1980年,他大力倡导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并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学术小组,被选为该小组的第一任组长,致力于推动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1982年2月,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分子反应动力学,借以在国内提倡化学物理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1995年前后,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大力提倡生物物理的研究,就如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进行这些工作和主持理论物理专项基金的同时,仍然亲自动手做一些感兴趣的理论研究。遇到适当的机会,他也和年轻人谈些治学的体会。他把学习方面的经验归结为四句话,即"学问主动,学友互助,良师鼓励,环境健康"。
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8月后,曾两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完成关于介子的HHP理论的研究。
